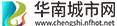# 沈静舟 | 瑾仙×我
# 当然要和美人甜甜地谈恋爱呀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 瑾仙这个角色是我从看小说时就唯二喜欢的角色(另一个是大师兄唐莲),该产出因为受到剧版影响,冒昧使用剧照为封面
【起】
“长宁可是你的同胞妹妹,你就放心她跟着瑾仙走了?”
“当然。”
“为什么?”
“因为那是十七岁初入江湖便鲜有敌手的沈静舟,二十岁入宫陪伴长宁十余载的掌香大监。他还是我两位老师的座上宾,仅凭这一点便能得到我的认可,更何况,他还长得好看!”
“不错!”我不禁抚掌大笑:“江湖上的传言就该是这样的。”
萧瑟却十分不耐,仿佛让他承认嫉妒瑾仙的相貌是件比从龙椅上站起来还艰难许多的事情,他冷哼一声道:“厚颜无耻。”
明德二十三年,历时三个月的无王之至随着永安王和大军的凯旋终于结束,先帝二皇子萧崇登基,定年号崇河。
崇河一年,春暖花开。
跟在萧瑟身后出天启的还有一辆金顶马车,车前挂着两盏灯笼,灯笼上各用金线绣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神鸟大凤,整体就差把“有钱、尊贵”四个字明晃晃地刻在轿子上了。驾车之人却不似这般直抒胸臆,他像在思考些什么,目光迷离,手中佛珠捻得毫无章法,直到听见别人喊他才勉强回过神来。
“沈静舟……”他轻声重复着,像是一句叹息:“倒是很久没有从旁人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了,永安王殿下。”
“似有仙人天上来,一剑既出风雪萎。如今你再入江湖,也算给这则传奇故事补了一个结局。”
闻言,他拱手行了一礼:“多谢永安王成全。”
“我不是成全你,我是成全她……”
北离疆域辽阔,从天启城往昆仑山去更是横跨整个东西,我正捧着地图研究这一路可看的风景,谁知聊天话题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我身上,只好撩开帘子试图打断他们:“萧瑟,你怎么还不走?”
萧瑟作势要拿无极棍敲我,“怎么跟你哥说话呢?”
我回了个鬼脸,“瑾仙,我们怎么还不走?”
被我叫住名字的人忽然笑了,他稳稳地牵住缰绳,应允道:“是,殿下。”
不管是瑾仙还是沈静舟,他做过最多的事便是听我的话。
【承】
我叫萧遥,永安王的双生妹妹,北离皇室唯一的公主,早逝的母亲是明德帝此生挚爱的白月光,他给我封号“长宁”,下旨不可和亲、不必联姻,四书五经六艺皆同皇子教养。唯在武学一事上,任由我们各凭心意选择启蒙师父。
那时,老七已入洛青阳门下,兄长也被姬若风领走,二哥与我面面相觑,最后让我先行挑选。我才十岁,便独爱这世间好颜色了,几乎一眼认准了跪在堂下的瑾仙——彼时他的名字还是沈静舟。浊清大监将人领到我面前,还不忘夸我眼光好:“长宁公主慧眼如炬,这位弟子此前一直在江湖游历,刚被奴才捉回宫来,武功技艺确实比旁的强些。得公主青眼,不若一道赐个名字吧?”
他们管上位者给予的叫做“恩”,不论喜欢与否都得磕头跪谢,可我选定的师父若对我低下头颅,又如何能让我信服呢。我摆摆手,道:“不必了,就按照内廷规矩,排行择字即可。”
下首却有人插嘴,“奴才斗胆,给公主出个主意。此人虽是男子,却有天人之资,何不以'仙'字为名呢?”话中的嘲弄之意昭然若揭,不论今日之事如何收场,必会沦为宫中笑柄。我自然气不过,呛他道:“你颇有几分眼光,'仙'之一字虽勉强与他相衬,倒是你,莫过于'瑾言'为名了!”
该怎么形容二十岁的沈静舟呢。
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让跪便跪,让谢便谢,像是个被他师父牵着线的木偶娃娃,仿佛深陷泥潭便在这泥潭中安了家,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生气儿。接任掌香监一职后,他成了众人口中的瑾仙公公,人们说他香调的极好,茶也是这宫中绝品,可我闻多也尝多了,总觉得那是按部就班堆砌的东西,像他这个人一样没有灵魂。
我去问他为什么,“难道你的心是空的吗?”
他还是有心的,不然不会被我一番话刺痛。沈静舟攥紧的拳头因用力而微微颤抖着,一滴眼泪滑落又被他不着痕迹地抹去,“殿下可知,师父派我到江湖中游历时,曾与我打过一个赌。”
这件事我当然不知道,因此我的回答无关紧要,但他还是停下来等着,就像他一贯的做法那样。我摇摇头,听他继续说下去。
“师父说,当他需要我时,会到江湖中寻我。如果我能将他打败,便可不随他入宫,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于是,我拼了命的练剑,去挑战那些世人眼中不可逾越的高手。现在想来,那是我在给自己壮胆,万一师父听了那些唬人的名头,便放弃了寻我的念头呢。江湖,令人心驰神往的江湖啊,可惜,我还是被他拧断了双腿带回宫中。”
沈静舟自嘲一般地笑:“与殿下初见时,我刚从病榻上起身。”
这下,换我的心刺痛了。
兄长直言我完蛋了,因为“心疼一个男人的时候,一个女人悲惨的命运便开始了,之后,这个男人就要玩弄女人的感情了。”
我觉得他在放屁:“他是太监,他不能玩弄我。”
萧楚河更为大惊:“你这次真的完蛋了!”
我不解:“为什么?”
他武功都不练了,凑上来一脸的不可思议:“你甚至不在乎他是个太监,你才十四岁,便要爱上一个人吗?”
我想了想,北离的女子十五岁便可许配人家,十六七岁为人母的亦不在少数,那她们不就应该在十四岁时与自己的丈夫相爱吗,总不见得都是一见钟情的姻缘。我将这个推论告知兄长,以此验证即使此时春心萌动也并不算特殊。萧楚河思量许久,突然发觉自己也才十四岁,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比我更多的发言权,这个话题方才作罢。
我虽不懂情爱,却知道善待一个人的方式无非投其所好。于是,便开始从父皇那里讨一些需要在江湖中解决的事务交予沈静舟去办。时间最长的一次我足有三个月没有见过他,以至于习武进度也落下许多,明明是与萧楚河一母同胞的天赋,兄长隐隐约约够到逍遥天境的边缘时,我仍在金刚凡境苦苦挣扎。
我为此烦躁不已,连带那年的春猎都不是很有兴致——若非信马由缰时不小心惊扰了一头刚从冬眠中醒转的青色大蟒。
那是明德十六年,按照随我出行的禁军的说法,是“公主像是有心事,不许属下跟的太近,所以那蟒蛇一跃而起时,属下未来得及反应,此后更是丢了公主行踪,只远远听到公主说,要剥了那畜生的皮做……做手衣。”
兄长对我指指点点。
想来那时的情况应该和禁军说的差不多,要不是惦记沈静舟那柄风雪剑寒气太重,谁会在被一尾巴拍到树上撞坏脑袋的时候还不忘死死按住插在大蟒七寸的匕首呢。
之所以说“差不多”,是因为我失忆了,不多不少刚好忘记了和大蟒殊死搏斗的全部过程。以至于醒来看到那副完整的皮草还挺兴奋的,四舍五入等于白捡嘛。
沈静舟回宫时,我还被兄长按在床上养伤,公主府的大小仆从被威胁一个遍,竟让他在院中跪了三天三夜而无人通报。直到我在睡梦中听见兄长的斥责:“我记得父皇是让你去寒水寺参加忘忧住持的就任礼,以示皇家对禅道第一大宗的重视。可是什么典礼需要三个月零二十二天?这么长时间你又去了哪里?!”
沈静舟仍然跪着,许是某天夜里下了不小的雨,他额前的头发黏腻腻地粘成一团,连带着湿漉的衣衫,看起来狼狈不堪。他却浑不在意似的,一桩桩一件件就差把自己的行程写成以时刻划分的奏本:“我去见了几位故交好友,与他们去昆仑山看了声势浩大的一场雪,我们在雪中比剑,夜里卧雪而眠,如此过了大半月。直到忘忧大师就任典礼将近,我才匆匆赶赴,还在佛寺哄骗一个叫无心的小和尚喝酒……”
我在门内安静地听着,却无端觉得他正艰难地、一刀一刀地将自己剖开,以这样近乎凌迟的痛苦去缓解心中的悔与恨,他开始仇视江湖中那个与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的沈静舟,不啻以最恶毒的言语诋毁他:“殿下为了给我做手衣和巨蟒搏斗受伤时,我……”
沈静舟咬紧牙关,过了许久才继续说下去,“我正因为要回宫而心伤,我的朋友在旁宽慰,说江湖再见……”
他重重地俯身叩首,颤抖不已:“瑾仙……罪该万死!”
兄长是将沈静舟放在了一杆秤上,问我还值不值得付出真心,可是“付出真心”本就是一个选择,且没有其他选择配与之相提并论。更何况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天启城是我的家,沈静舟只是不喜欢这里而已。
话虽这么说,双腿却没来由地酸软,若不是身为公主的矜傲迫使我死死地抠着门扉说不得真一屁股坐下去。兄长就在此时错开身,让他一眼能够看向我。
沈静舟的眼眶瞬间红了,想起身去扶我,又被负罪感订在了原地,几番拉扯之下,忽然咳出一滩鲜血。他不堪重负,声嘶力竭:“殿下!”
从此事后,沈静舟再不肯接手那些我给他揽来的事务,反而暂代了鸿胪寺卿,一幅要扎根天启的模样,我不明白,便去缠他要个说法。他惯常是个安静甚至寡言的人,调香烹茶时更忌讳旁人在侧叽叽喳喳,当然,我是不算在这个“旁人”内的。
可不知怎的,那天沈静舟脾气格外火爆,我刚叫了两声他的名字,他便将打香篆的灰压往桌上一撂,不悦道:“我是瑾仙,不叫沈静舟!”
这怒气来得莫名,我撑着桌子细细打量他的神色,“你在和我生气吗?沈静舟。”
他终于肯直视我的眼睛:“我是在和自己生气,殿下。殿下总唤我沈静舟,以至于我差点忘了,我已经是瑾仙很久了。”
“你是谁是由名字决定的吗?那我偏要这样叫你,沈静舟很好,你不能忘。”我再次强调:“我第一眼见你,就觉得你很好。”
所以不忍见你以身陷泥潭、被困笼中鸟。
沈静舟抬手轻轻碰了我的脸颊,“人虽不能由名字决定,身份却可以,我是瑾仙,这对你我二人才是好的。”
他不再是浊清大监手里的木偶,他想成为我的一件玩物。
我被这个念头吓出一身冷汗,接着便大病一场,一直病到琅琊王叔谋逆、兄长被贬为庶民流放青州。强撑着求见父皇时,父皇仍高高坐在龙椅之上,只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搅扰得疲惫不堪,我的问题他一概不答,反而说:“你想招一位驸马吗?”
我使劲摇头。
他却闭上了眼睛:“下个月殿试大选就开始了,到时候你来,找个合眼缘的,孤为你们赐婚。之后相夫教子都随你开心,只有一点,别再搅进这件事中。”
父皇叫我不要胡闹,我偏就胡闹给他看。于是仗着母亲、兄长遗留的荫庇,一头扎进沈静舟的鸿胪寺中,任凭外面找我找到天翻地覆,我只枕着新调的安神香睡一场春秋大梦。
不是没人来过这里。
我对沈静舟说,我不要选驸马。
甚至不需要掉一些可怜巴巴的眼泪,他便应允道:“殿下,你不用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等再醒来时,沈静舟仍陪在榻前,只是脸色比方才惨白许多。
“父皇罚你了?”我问。
答案太显而易见,我被自己逗笑了,而后慢慢起身、慢慢靠近他,极轻极浅地在他唇上印了一下。
沈静舟没有惊讶,像是早就知道我会走到这一步。他将手指轻柔地覆在我的眼睛上,从耳畔传来的声音也带着哄骗的意味:“殿下不怕。”
后来父皇果然没再提招驸马的事情,沈静舟身上也被牢牢烙印上了长宁公主的痕迹,我不清楚睡着的片刻时间发生过什么,想来不过验证了兄长临行前的一句告诫:“要成为不可替代的人,才能保你周全。”
所以父皇不敢杀鸿胪寺卿,也不忍罚我。这样的日子太漫长,我几乎依靠沈静舟的百依百顺才度过那一段艰难的时光:我的兄弟各自为营,我的父亲屡屡透过我看向他失去的两位挚爱,我不能耀眼、不能平庸,还要在这狂风四起的天启城中代表永安王为雪落山庄抵挡无处不在的暗箭,为琅琊王叔的旧部撑起保护之伞。
沈静舟就在此时入了逍遥天境,也越发得父皇器重,直到后来我的存在无足轻重,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掌香大监的选择。他仍然说,“瑾仙没有选择,我的站位只在殿下目光可及之处。”
【转】
我们的曾经在纷乱的史书与年号更迭之中。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始于店小二眼中不知所谓的争吵。
“一间上房。”
“两间!”
“一间。”
“本小姐千金之躯没把这客栈包圆了已经很掉价了,怎么能和你挤一间屋子!”
“殿下屈尊纡贵在鸿胪寺那处小榻休憩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怎么现在开始讲究了?”
我大惊失色:“瑾仙,你之前不这样的。”
沈静舟年少成名,境界却始终距逍遥一线之隔,后来他顺利破境,也曾提过或许是更加坦然不再纠结名字与身份之论。即使如此我在宫中也甚少叫他瑾仙,可这个名字实在太美,如今抛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得已的时光,更格外与他相称,叫出声后堪称唇齿留香。我不动声色地回味一番,也因此错过他的一句什么话。
瑾仙默不作声地与店小二将房钱钥匙交接好,便牵着我往楼上走,直到进了门一把将我抵在墙上。他说,“我才要问你怎么了,殿下?”
我不想走了。
这个念头一生出来,眼泪几乎同时喷涌而出,瑾仙慌了,下意识就要将它吻去。
我哽咽着,却推不动他,只好挡住自己的脸:“我涂了若依送的鸭蛋粉,不可以……”
“殿下,别管什么鸭蛋粉了,”他难得如此强硬,温热的鼻息打在耳旁,激得我一阵颤栗,“管管我吧。”
…………
瑾仙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他传书给了萧瑟,兄长又喊来了华锦小神医和叶若依等一行人,他们浩浩荡荡挤进了昆仑山脚下我们驻足的小客栈,只是我的精神越发萎靡,没陪他们说两句话就困顿得睁不开眼睛。
瑾仙将我拥在怀中,一边细细回想出宫后的诸多症状,一边盯着华锦给我切脉。
“长宁比我在宫中见她时瘦了许多。”
“起先我以为是路途奔波所致,现在看来不是的。”
“她早年受过伤?”华锦肯定了自己的推测:“伤及肺腑,且一直没有痊愈,又劳思过重……怪不得总给我一种腐烂的种子的感觉,表面毫无损伤,其实芯子已经坏透了。如果不出我所料,她会在接下来半年的时间慢慢陷入沉睡。”
瑾仙心头一紧:“可有法子医治?”
“药石罔效。”华锦沉吟片刻,又说道:“这是心疾,或许,一剂真心可救。”
他忽然就笑了:“瑾仙身无长物,唯余真心矣!”
【合】
我被封印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盒子里,四下无人,一片静寂,喊也喊不出声、走也走不出去。终于我累了,就瘫坐在那里,想:沈静舟此时在做什么呢?兄长认百晓堂堂主做师父后,曾调查过沈静舟的过去。他幼时尝尽亡破之苦,为躲避命运在昆仑山上勤修六年,这个时间原本可以更久的,只因目睹山下一座村落被马贼侵扰苦不堪言便提剑踏着风雪而去,那时,就有人说他颇有几分佛性,适合掌香监一职。佛的怜悯不仅给予那些与他有着相同遭遇的人,沈静舟还曾一剑劈开州府强占新娘的婚房、冰封洪流肆虐呼啸的堤坝,百晓堂给他的评价是:风雪之中,自可见风骨。
想他想得太多,我开始忘记自己,等记忆的尘沙淹没过名字的时候,我想,就该把沈静舟送还江湖了,那个骑马斜倚桥、满楼红袖招的——他的江湖。
可是总有人不遂我愿,他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呼唤:殿下,殿下……
昆仑山终年下着雪,雪落下千年都不会化。
后来,一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百天宴,宴会空前绝后震天撼地,引得江湖各路人士纷至沓来,山上人满为患。那孩子叫萧张,他的父亲是永安王萧瑟,师父是天外天宗主无心,义父是红衣剑仙雷无桀,亚父是雪月城城主唐莲。
宴会结束后,萧瑟不满地对着眼前人:“我说,你至于一直在这山上隐居吗?冷死了。”
“昆仑山与我剑意相和,我在这里修炼,事半功倍。”说话的人依旧面如冠玉、风度卓越,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开心事,言语带着笑意:“而且,她也很喜欢这里,我觉得,她要醒来了。”
萧瑟朝屋内看了一眼:“我当年一走了之,劳她为我承担许多,内心是很过意不去的。”
“要我反过来宽慰你吗?”
“不。沈静舟,”萧瑟威胁似的眯了下眼睛:“我得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然的话,唐莲师父刚改良了那味孟婆汤的酒方,便是海外仙山我也可再去第二次。”
被称作沈静舟的貌美男子依旧笑着:“她不会愿意跟你走的,她爱我。只是我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太监,不太知道该如何回应,从前,也只是尽到一个被爱之人的本分。如今你既然问我了,那么,我与她相爱。”
昆仑山从来没有这么吵过,也从来没有这么静过。
我推开房门。